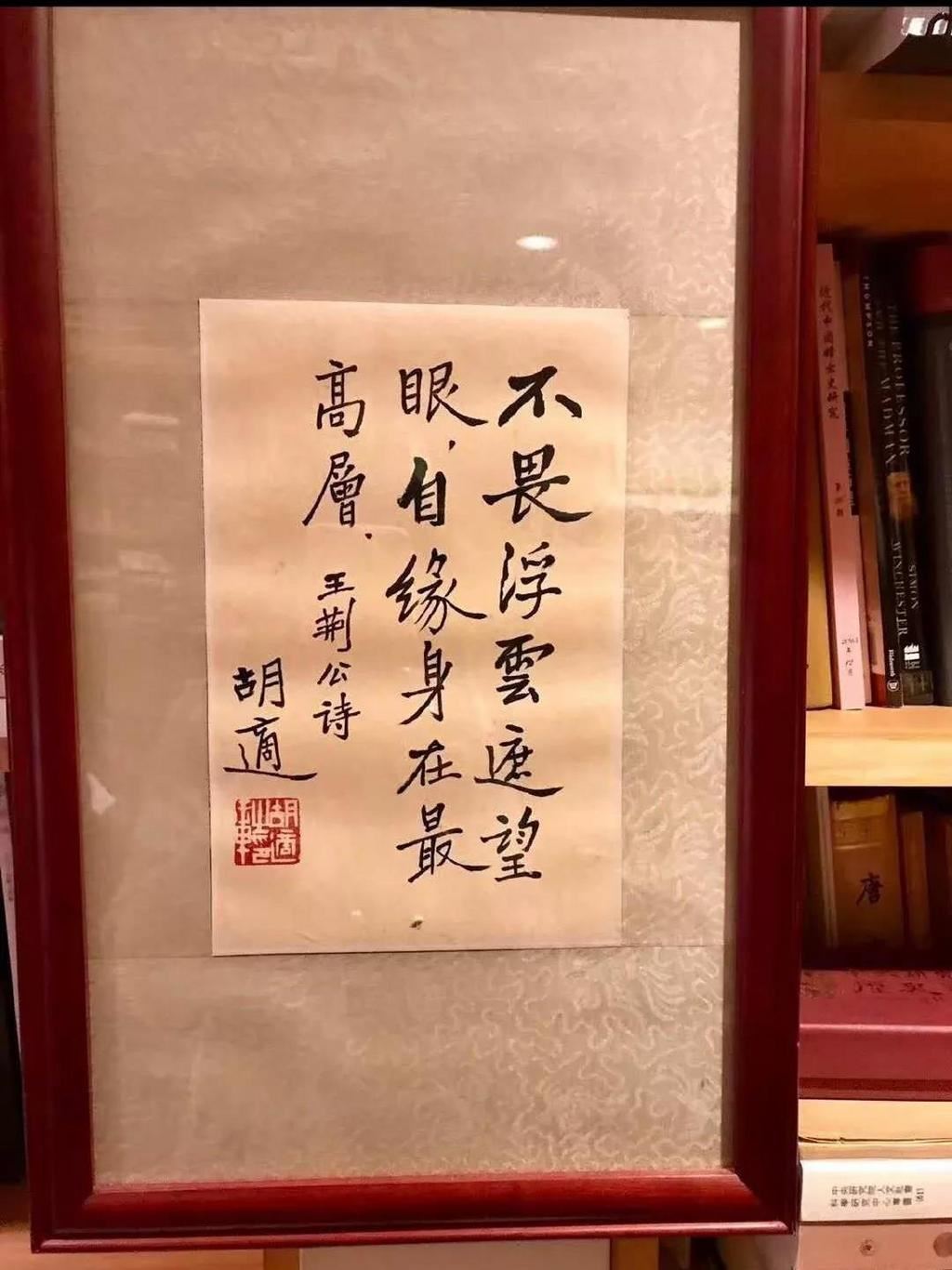可笑的是,我在香港幾年雖在所謂「第三勢力」刊物上寫過不少文章,卻從來沒有一個字涉及果皿擋。我的作品主要是從歷史角度倡導皿煮籽油的價值,上面已經說過了,不必再談。
我的困局當時在香港傳布得很廣,最後連亞洲協會駐港代表艾維也知道。艾維很尊重賓四師,一九五二年亞洲協會出資試建新亞研究所便出自他的決定。因此他通過賓四師,傳話要我去和他當面一談。在瞭解了全部情況之後,他自動地寫了一封信給美國駐港總領事莊萊德(長期在台北任美國駐華大使),指出我到哈佛訪問是一個青年學人一生難得一遇的進修機會,不應因技術性問題而喪失。於是莊萊德在覆信中提出了另一個給我入境的合法方式:我在香港找一位律師,當面宣誓自己是「一個無阈籍之人」,再由律師寫成正式文件,簽名其上,以代替護照,霉果領事館便可合法地在這一文件上簽證。
這一「無國籍」的身分給了我很大很多的困難。我每年都必須到移民局去申請延長,當時持有這一特殊身分的人似乎不多,移民局官員每次必詳細追問,並一再警告我不能離境,一離境簽證便失效了。這一情況直到十幾年後取得永久居民的身分才告終結


我的困局當時在香港傳布得很廣,最後連亞洲協會駐港代表艾維也知道。艾維很尊重賓四師,一九五二年亞洲協會出資試建新亞研究所便出自他的決定。因此他通過賓四師,傳話要我去和他當面一談。在瞭解了全部情況之後,他自動地寫了一封信給美國駐港總領事莊萊德(長期在台北任美國駐華大使),指出我到哈佛訪問是一個青年學人一生難得一遇的進修機會,不應因技術性問題而喪失。於是莊萊德在覆信中提出了另一個給我入境的合法方式:我在香港找一位律師,當面宣誓自己是「一個無阈籍之人」,再由律師寫成正式文件,簽名其上,以代替護照,霉果領事館便可合法地在這一文件上簽證。
這一「無國籍」的身分給了我很大很多的困難。我每年都必須到移民局去申請延長,當時持有這一特殊身分的人似乎不多,移民局官員每次必詳細追問,並一再警告我不能離境,一離境簽證便失效了。這一情況直到十幾年後取得永久居民的身分才告終結